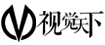作者_马萧
小桃寄来黄先生的新书,嘱我写读后感,这是第三回了。我喜欢永玉先生,被她知道,一来二去成了朋友。于是每有先生新书出来,她都寄给我,顺便说,要不写写读后感?
我也随口答,好的好的,待拿笔,又不知道怎么开头了。断续写过几稿,都是中途而废,不敢告诉小桃,只希望时间长点,她慢慢把这事忘了,这一页赶紧翻过去。小桃说:“黄先生喜欢年轻人读他的书,你写了,我给先生看。”于是我又鼓勇写,上周看看框架差不多,想着这周再润色一二,赶紧交稿。欠稿真是压在心上的石头,急需驱除,何况无论如何,写永玉先生我肯定是写不好的。
昨天下午五点过,极平常的时间,还没到微信高峰推送的时段。一个消息弹出来,“黄永玉去世,享寿99岁。”我愣住了,不肯信。不信一个99岁老人的去世,只因他是黄永玉。各大媒体的微信公众号陆续发了消息,短的如同讣告,长的回顾了先生的生平与艺术。我一一看完,发给小桃一个大哭的表情。
哀恸遗憾,在我今年是第二次了,本来要给师兄写篇文章,却是他再看不到时我才动笔。永玉先生当然不会期待我的文字,但在我一面,却增了愧疚。平时下笔,郑重是种负担,但郑重宜于哀思,宜于在哀思中平复情绪,清明神智,这下我便以郑重来告别先生。
从哪里说起呢?永玉先生是画家,也是作家,也是玩家。三者似分而实通,互相鼓舞,彼此成就者,先生当之也。名人常被笼罩在光环之中,以种种传说包裹,玩家尤见豪华、洒脱——永玉先生画猴票,画酒鬼,最早天价卖画;治豪宅,有夺翠楼、玉氏山房、半山楼,万荷园,老子居;藏烟斗、名表、嘉木、珍玩;八十开跑车,上时尚杂志,与时俱进;明星名士达官显宦,络绎往还,如此的交际圈和影响力,二十世纪的画家中,只有张大千可以媲美。以玩家的性情画画,爱用大笔,爱敷艳色,代表作是《大画水浒》,画鲁智深倒立着,酡红如重枣,大剌剌写一句题款“赶出五台山,还有一指禅”;画宋江题“凡事总是酒醒后才明白”;旱地忽律朱贵题“酒上不倒肉上倒”;画西门庆“整整一部四卷本为他一个人,你说他了不了得?”
永玉先生自述生平,以写作为第一,雕塑、绘画随其后。他的写作当然受表叔沈从文影响,1979年岁末率先完成的长篇散文《太阳下的风景》,也是写湘西,一面世立刻流行,翻印再三。八十年代,获新诗大奖,与诗坛老将新秀并肩。此后有诗画对照的《永玉六记》、《罐斋杂记》、《芥末居杂记》、《吴世茫论坛》,蕴藉机锋于笑骂中;《比我老的老头》、《这些忧郁的碎屑》则是散文的逸品,以画家之眼白描,局部入手,独取神貌,顽皮又深情。
以上或仍可归入画家的余兴、玩家的潇洒,我这时对他的喜欢,是那种带着尊敬的喜欢,有点距离的喜欢,没有到入迷的程度。但自传体长篇小说《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》则令人肃然起敬,而且亲近多了:原来这个豪华的玩家,一直还是湘西那个顽皮的少年。逾百万字的长篇三部曲,以湘西方言写故乡、闽南话写流浪、上海话写成长,跌宕生姿,在二十世纪中独树一帜。先生的写作,暮年愈见奋发,豪宴客散,泡茶点起烟斗,立刻能静如古僧,笔端往事汩汩流淌,于是玩家敛迹,作家现身。玩家的生平,写在文中,当然跳脱痛快。而玩家的另一面,则是常人不及的深情,惹人动容。他的基底正是深情,来自于湘西泥土,像画画时的底色,其上才是修养和阅历养成的胸中丘壑。再往上,才是纵意的才气,脱略的神态,不过像山间云霞,增声色之灵动。《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》完全地袒露了这样的基底,作为他全部文学作品的索引,只要把张序子代入同样年岁的黄永玉,就即刻勾连篇幅,充盈情思,从他的杂文、短篇、漫画中闪现的光芒,也因此获得解答,原来他是这样的人哪。
小桃赠我明黄耀眼的《见笑集》是诗集,天马行空,采撷岁月的露珠,篇幅和文体,都是与《无愁河》对立的极端。细看,细读这露珠里折射的饱蘸的情思,人事,说尽而不尽的愁滋味,像我们也寄身于一个苍茫又青翠的灵魂之上,有了一段跨越生命的漫长旅程。《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》,是永玉先生唯一一册近乎正剧的文画合集,既是行旅手记,也是对于美术史上诸位大师的一番致敬。这些地方,大师的灵魂不止在博物馆的作品中,也在那些不怎么改变过的街道、屋舍和草木河流间,在那些旁观者的善意里。
我这才回头认真去看先生的画。北京画院的“入木”,是他早年版画的集萃。《春潮》好生厉害,他怎么把线条变得这么有弹性,几乎溢出边界,四散奔逃?他刻大兴安岭的一角,猎人在溪水边,植被怒生,密而不乱;《阿诗玛》的洋气和古典,侧面挺秀的鼻尖,我有一阵常常信手练习侧面的轮廓,原来潜意识在模仿她。难说他是取法丢勒、明清木刻,还是鲁迅先生引入的现代木刻,但在一众左翼青年中,以浪漫、清新见长,功力扎实,但绝不自拘一格。玩家藏着的身手,天才的用功,也是在他的自传里的插图才揭出答案:张序子背着几十斤的木板和刻刀的巨大行囊,拔足远方——当然如此,必须如此,这有什么奇怪的呢?永玉先生会说,几万几十万的刀痕下去,不这样还能怎样呢?后来一层层破局,衍出的种种奇崛险峻,包括意大利巴黎的钢笔淡彩,各种水墨漫画,大泼墨的重彩荷花,包括年初古怪的蓝兔子,岂非顺理成章?
我与先生仅一面之缘。去年去黄永玉诗和插画展,我到得早,先看一遍作品,轻声读诗。午后三四点先生来了,坐在轮椅上,被人极慢极慢地推着走,平和地跟熟人点头,间或停下,对着画说几句。我远远望着,想着刚刚看到和插画和诗,心中错愕,总觉得这副衰老的身体是他的伪装。还有这样茁壮创造力的人不该这样,这是他跟大家开的玩笑。他应该脱下这身衰老,从轮椅里跃起,大笑,说湘西口音的京片子。后来,不时从微信公众号中看到视频,永玉先生坐在花园里读新作的诗,声音很轻,像在喃喃自语,又像民国老电影里的旁白。身边的猫卧着,懒散地享受。
小桃寄来最新的书,非正式的印本,名字从背后一直飞到封面,《还有谁谁谁》,翻一翻,近两年写的,全是新作。写的那么细,记得那么清,笔力那么劲健。谈掌故,谈故友,那样有滋味,没有力气和心力,哪能这样写。我没老过,不懂老,但见过许多老人,老人没有永玉先生这样的。天,我又想起那个缓慢衰弱的老人。不对,他一定是装扮好了应付各种视频和活动,把自己弄得像个百岁的寿星,对大家有所交代。真到了独处的时候,卸下所有的装扮,这才点起烟斗,怡怡然下笔如飞。
可是他竟然走了。《还有谁谁谁》的序里,他说“现在离一百岁还有一年多时间……万一活不到那个时刻,看不到自己的画展,当然有点遗憾,那是老天爷的意思,谁也帮不了忙。”这样说话,显然是客套,怎么老天爷当真了?我突然又想,他大概是自己扮演老人不耐烦了,于是纵身跃起,到了天上。
2023.6.25