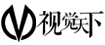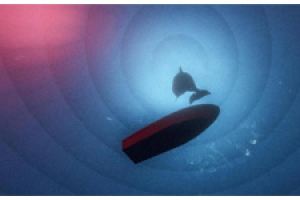文/罗韬
石丁早年学画于齐鲁间的名家,后追随央美张立辰和于光华先生左右,主修山水花鸟,不仅能书善印,尤以画鸡见称。他画的鸡,奋啄斗啼,都可谓穷形极态,跃跃然如来就人。其中最佳者,雄视顾盼,有一种凛然不可犯之气,如见京剧舞台上之关公关云长,不怒而威,看到这里,我不禁拍案叹赏。称之曰:得。

谢赫《画品》有云:气韵,生动是也。此语居“六法”之首。但是,对于翎毛之类,生动仅是画家的能事而已,还不是画之极境。那么,什么才是翎毛类绘画的极境?司空图《二十四诗品》之中的“精神”一品!王安石诗:丹青难写是精神。此语最妙。那么,精神何来?仅是画得生动肖似而已?非也!我对精神二字的解释是:既取物之精,复赋我之神——既能抓住所描写的动物的特征,又反映出作者自己的思想气质,是客观之物对“我”内心有所刺激而产生的图景。为什么有人说,黄胄的驴还是畜牲,而徐悲鸿的马,有古君子之气质。这不是说黄胄的驴不生动,他有过人的造型能力,又娴熟于水墨,但是其中就是缺乏一种精神的内涵。这就是黄胄驴与徐悲鸿马的差距。也就是我所说的精神才是评判绘画,尤其是评判翎毛等动物画的最高根据所在。

而对鸡的诠释,其实是对一种人格的诠释。有些画家,以生动为宗旨,好描绘雄鸡的好勇斗狠,啄极尖,爪甚利,颈毛倒竖,阳气过刚而余味短乏。齐白石老人画鹰,多喜表现苍鹰平和闲静的一面,足令观者赏之思之。鹰尚如此,何况被称为”德禽”的鸡呢?当一个画家画雄鸡,画出京剧中的“红生”的气质,就可谓得之矣!京剧以“红生”来表现关羽就颇值得深思,红生在老生与花脸之间,既有老生的庄重,又有花脸的沉雄,但又克服了老生的文弱和花脸的刚猛,所以,有“红生鼻祖”之称的王鸿寿演关公,既肃穆庄严又威武激昂,令人回味无穷。徐悲鸿写马,如写古之君子;而石丁画鸡,几如写红生,神武而文,不怒而威,其可谓得之也乎!
罗韬